大学毕业后,我在煤矿车间当工人|三明治
来源网站:m.163.com
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找工作, 车间, 分配, 母亲, 厂里, 班组
涉及行业:采矿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福建省
相关议题:考试, 肮脏或危险的工作环境
- 文章描述了在煤矿车间工作的艰辛和困难,包括噪音、灰尘和脏累的工作环境。
- 毕业后进入矿务系统的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待遇不同,职业前景也有差别。
- 作者提到了通过考试招聘进入矿务系统的工人身份,对于那些技校毕业直接分配的工人来说,工种可能更好。
- 文章中提到了一些人通过后门进入矿务系统,但这种机会非常有限。
- 作者描述了自己回家后找工作的困境和不确定感,以及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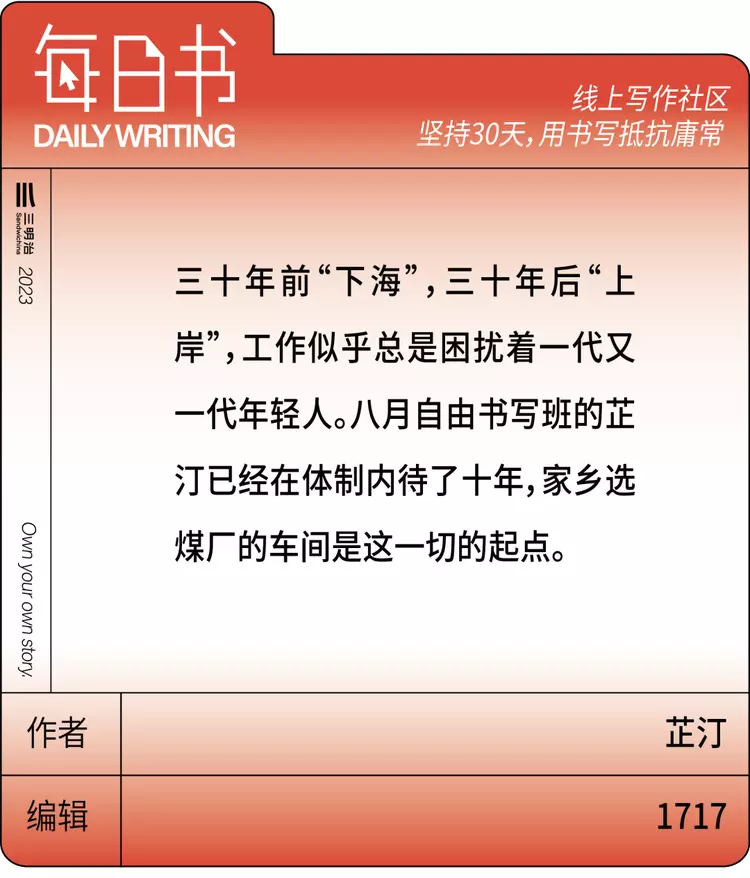
我还记得刚工作时待过的那个车间,称为“重选车间”。这是一个最先和原煤(从地下直接开采的没有经过加工的煤)打交道的地方,大约需要经过上料、往煤炭中加入洗煤介质等,加工过的煤才会进入下一个工序。
只要机器在运转,就有轰隆隆的震天声,说话都靠吼,有些年纪大的员工会耳背,长久的噪音导致。轮到夜班时,机器运转正常的话工人们可以在厂房休息室的长条凳上轮班睡上一两个小时,只要保证每个岗位上有人清醒着就好。习惯了在噪音下入睡的老员工,如果哪天夜班赶上机器检修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厂房需要“停车”,他们就没办法安心入睡,因为太安静了。
在重选车间上一个班,即使口罩裹得严严实实,下了班依然是灰头土脸,鼻腔里充满黑色的煤灰。车间的窗台上也铺满一层厚厚的煤灰,机器的表面挂满灰尘。上完一个12小时的班,必定会先洗澡再回家。
那时的我经常在值夜班的后半夜从车间的窗户往外眺望,看着天空的颜色一点点变化,蒙蒙亮,微微红,染红一整片天边的红,然后大亮。偶尔绝望到谷底,从二楼往下,看到那个贯穿两层楼深的充满粉尘泥浆的黑暗的大池子,人生变得黯淡无光。
苦熬着的一切逻辑是这份工作是一个正式工,这一点对于我们那座煤矿城市的人来说很重要。也是许多没有工作的人的梦寐以求。
01 毕业
我大学毕业那年遇上金融危机,工作并不是太好找,当然我也没有认真地去找工作。
毕业前夕我在去留之间陷入两难,是留在省会城市还是回到家乡,我挣扎纠结,拿不定主意。同学们有的等着去读研究生,有的等待来年再战,有的搬去学校周边的小区过渡再做打算,也有在毕业前疯狂的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租房子。我们寝室比较佛系,只有一个室友早出晚归出去找工作,其余的都不着急。那时我们感慨自己学的专业“很垃圾”,一点也不专业,我们好像都不具有找到一份好工作的能力。象牙塔里待惯了,没有了学校这道围墙的庇佑,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社会。
后来我做出了回家的决定。我不像是一个迫不及待踏入社会大显身手的毕业生,而仅仅是一个结束一段求学生涯的旅人,一个踏上回家归途的空白者——对未来的规划脑袋里一片空白。
火车票应该是提前买好的,那时还不可以网上售票。一趟超级便宜划算的绿皮火车,几乎跨越半个省份的距离,价格只需24元,大约运行四五个小时。现在再也坐不到那种绿皮火车了,旧的,慢的,不那么着急的,载着旧时光的。
火车把我载到了家乡,也把我推向了社会,面对社会我是被动的,不适的。好在家作为缓冲地带,承接了我的手足无措。母亲说让我在家休息休息,读了这么多年书。我也偶尔跑跑人才市场,递递简历,大约还参加过一个银行的面试,好像也没下文了。留在省会城市的同学约我去某快餐店当服务员,底薪700元,我想去,母亲不让。
大约在家待了1个多月,家里的座机响了,母亲接的电话。说厂里(我们那的厂矿企业)组织部找我,问我要不要参加矿务局组织招聘的考试,针对矿务系统近两年毕业的职工子弟。
我考上了,和我一同考上的还有六个高中同班同学和两个小学同学。
矿务局是个矿务系统,属于国企,下辖20多个煤矿和若干洗煤厂。我们那年分配是属地原则,你来自哪个矿区还给你分配到哪个矿区。我家是洗煤厂,所以我理所应当地被分到了厂里,和我父母一个单位。我入职那年母亲50岁刚好退休,父亲仍在职。当然也存在特殊情况,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男生就没有按属地分配到我们厂,而是去了一个有升职希望的新区,还不用下井。他爸爸早年做生意,有钱,可以帮他去矿务局总部活动。
我进到厂里,为我此后无尽的痛苦绝望和对父母无休止的抱怨和无理取闹埋下隐患。
02 分配
7月毕业,8月考试,9月份就已经入职了。我和一个小学同学女生,还有一个托关系找后门的男生一起被分配到选煤厂。为什么说他找后门呢,因为他的家在矿上,他本该分配到矿区,但分配到矿上的男生可能就面临着下井,所以托人分到厂里,最差也都是地面的工种,最脏最累的活大不了就是车间。
即使同是车间,不同车间工作的轻重程度和作业环境存在着很大差别,因为洗煤的工艺流程不同。虽然大部分的洗煤工序都是机械自动化,但也需要人工。我自己待过的是“重选车间”,要最先和原煤打交道,上料,洗煤,加工,每天轰轰隆隆,灰头土脸,总之“很脏”。加工后的煤再进入“浮选车间”,具体的工艺流程是什么样的,我不得而知。两个车间虽在同一个厂房,但如果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里,会感到明显不同,浮选车间无论是噪音强度还是空气中漂浮的粉尘都要小很多,偶尔从他们车间路过就感觉好干净。
我的小学同学就分到了浮选车间,我则被分到了重选车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成了我此后一段时间内和父母抱怨的说辞之一。我埋怨他们为什么当初没有找人,因为后来听说小学同学的父亲提前找了关系,那个同学才得以分配到那个车间。
工厂里新进的年轻职工一般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技校毕业直接分配,技校也是矿务系统内的单位,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矿务系统的职工。毕业生被分到各个厂矿区,身份多是工人,如果不走后门一般会被分到生产一线干比较脏累的体力活。家里有人的话分配的工种可能好点,比如不用下井,不出意外的话就干到退休。
还有一种是每年毕业季,企业到煤炭相关高校招聘对口的大学毕业生,这种进到企业就是干部身份,最低也是技术员,他们在矿上以后是当领导的后备人选。
除了技校分配和对口高校招聘的,还有我们这种通过考试招聘进来的。虽然也是本科毕业,但因所学专业不对口,身份也不同,前者是干部,后者就是工人,进到企业后直接去一线,没有所谓“高校光环”。当时也会忍不住抱怨不公平,但没有人会听你说这些。
最后一种就是纯粹走后门,但很难很难,非一般人可以做的到。我考上的那一年妈妈朋友家的女儿就这样忽而进入了矿务系统。她妈妈是在所有的事情都做妥之后才往外宣扬的,一是表达自己的女儿也不差,有了工作,二是低调炫耀自己家背景很硬。她的叔叔还是大爷是矿务局某某厂的一把手,硬生生把她安排进去了,当然不会是干部身份,是工人,但干着较轻松的活。
工人和干部身份不同,待遇也不同,以后在矿上的职业前景也差别很大。但总的来说能进矿务系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毕竟算是铁饭碗,矿上分配的女技校生找对象都比较吃香。一般情况下人进去就是一辈子,不会再跳出这个圈子,我父母就是如此,我姑姑小叔他们也是如此。
现在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在车间里当工人作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同事们对我真的很好。只是在最初的新鲜劲褪去之后,我开始不适应,我的大学同学们可没有一个要在车间里头上夜班。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苦撑着,我无时不刻不想着逃离,但更多的是抱怨,对父母的抱怨,我抱怨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找人调换工作,为什么看着我这么痛苦,却还让我去那里上班。
那时的我开始怀疑人生,变得敏感易怒,母亲经常只是默默承接了我的无理取闹,歇斯底里和对他们的大吼大叫。因为她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想激烈反抗,但听不到声音。即使听到了也毫无用处。躯壳还在那里,还在那个环境里。
03 车间
重选车间是全厂公认的最累最脏的车间工段。工段又分为几个小班组,其中的原煤班组是最先和煤打交道的班组,是重选车间最脏最累的班组。一个不在车间工作的、坐办公室的厂里的其他人如果犯了错误,惩罚的手段之一就是分配到原煤班组,像是“下放”。
我被分配到重选车间的其中一个班组。班长是和我母亲差不多大,是个女班长,这在车间里很是罕见,一般当班组长的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女班长姓熊,我们亲切的称她为“熊班长”,据说她的力气很大,干起活来从不输男性,班组里人都服她。
一个班组大约十一二个人,老员工占六成,年龄多在45岁以上,除此之外加上我一共四个25岁以下的女孩子。领了工作服和安全帽,班长指定一个40+的女性员工当我的师傅,姓苏,人很好,永远扎一个马尾辫,说话总是笑眯眯的,我总觉得她单纯。
班组里的人对我都很好,生产一线的车间里几乎没有大学生,当时我是整个重选车间的唯一一个。一开始他们觉得新奇,不让我干很重的活,甚至偶尔还会把我当成小孩子。那时的我刚毕业,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对车间里的一切也都觉得新奇,常常抱有一种好玩的心态。我回家会和母亲笑着说单位的事,比如我和母亲说我从没见过车间里那么大的铁掀,我单单是拿起来都吃力,别说让我用铁掀铲煤了。而师傅们可以毫不费力一铲一铲满满的往传送带上送掉落的煤炭,我不行,三分之一铲都很费劲。后来师傅们干脆把最小的铲子让给我,这样我便轻松了许多。
在车间里大约工作了一年多。我在脑袋里反复回想这一年,我学到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现在我能给自己唯一的确定的答案就是我遇到的那些班组成员,无论是和我父母年龄相仿的老师傅,还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同龄人,他们真的都很好,对我也好。他们干起活来不会藏着力气,虽然从事的是辛苦的体力劳动,但同事们的关系融洽,不会藏着掖着或背地里使坏。大家的相处是开心的,脸上是有笑容的。
是我自己,到最后身体和精神处于接近崩溃的状态。经常下了夜班回到家却无法入睡,或者浅浅的睡一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可能会发很大的脾气,通常是对父母。生活的半径变得狭窄,我把父母当做庇护我的羽翼,同时又对他们不满。我不满他们没有能力给我调动工作,就那么看着我忍受痛苦。我想如果我有了孩子,我绝不会这样。我绝不会看着孩子那样忍受煎熬。父亲大部分时候就是缄默,母亲只是在生活上更加照顾我。但这一切填补不了我内心的黑洞。
04 逃离
我竟有些不愿回忆在车间上班的最后日子,我想模糊它们。反正后来有一阵子我就不去上班了,我以考研为借口逃避工作,结果没考上,我挺丢人的。
后来厂里的后勤部门招人,班长和我母亲说可让我报名去那里上班,不用在车间,也不用上夜班,还是正式工,就是工资少一点,不那么体面而已。我就稀里糊涂的去了厂里的后勤部。第一次开会,领导坐在上边,别的话全忘了,记忆犹新而且刺痛我的是,他说有四类人会待在这里。一类是身体不好的,一类是脑袋(精神)不好的,还有就是为了照顾家庭在工作上已无所求的女人,剩下一类忘记了,反正大意就是但凡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到这里来。
我在想我是属于哪一类,难道是属于精神不好的。我可能是那里面唯一的大学毕业生,领导说的那些话挺刺激我的,不过那时也是别无选择,无路可退。那之前我已经请过病假、也离家出走跑出去找工作,不过最后还是回来了。精神几度崩溃,那时的那份工作对我来说是回归正常的生活。
说是后勤,其实具体就是打扫卫生的工作。
这工作我大约做了一年多,中间谈个男朋友,前后几个月,后来也分手了。一个高中同学过年期间约我逛街,她说准备考事业单位,说比考公务员容易一些。那时我固执地认为公务员我考不上,竞争压力太大,一听说事业单位容易考,我开始有意无意的关注省考信息。在那之后没多久,省考信息在网上挂出来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还真有招我这个专业,地点在X市,只招一人。2月底才出的信息,3月底考试,我去市里的书店买了事业单位联考的书和试卷,认认真真准备了1个月。
3月底到X市参加笔试,5月面试。面试结束离开考场,等再进去时就是宣布分数。他们说我是全场最高分,我很激动,走出考场我眼泪就下来了。
10年过去了,我仍然在体制内,但在这10年当中我想过无数次的离开。对我来说迷茫是人生的常态,我常常迷茫。个人的能力也存在短板,也不完全是指工作能力,包括成熟的能力,稳定情绪的能力,和人打交道的能力等等。我想我留在这里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就是按部就班,在碌碌中伴随着时间流逝。
但如果一个人和我说“你把编制给我吧”,我想我是不会轻易答应的。现在的编制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付出劳动可以换取养活我自己和孩子的收入。所以即使有时候生病身体不舒服,我还是会去上班,即使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要吃母乳,我还是会到点才走。哪怕半小时我也不敢提前走,我怕对不起自己的工资,也怕别人说闲话。
偶尔心里会泛出一些无力感,对一些无法把控东西的无力感,对一些明明觉得不对又无法改变的无力感,又或者是自我否定的无力感。我尝尝会自我否定,没有自信。
也许我是幸运的,我拥有了编制,我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我可以裹腹。人生有时候也是机缘巧合。
那时的编制没有那么难考,那时的考生也没有那么卷,那时的就业形势也没有那么严峻,那时的工资也没有那么高。
05 如果
如果我没有考到这里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在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变成那位在台上领导口中的精神和身体都不正常的那种人,因为持续的内心落差和对自我认知的狭隘视野,这些情绪靠我一个人走不出来。而当时的我又是那么封闭自我,除了抱怨什么也没有,父母也帮不了我。长此以往心理一定出问题,久而久之人也就出了问题。
除了工作,当时还有一些无形的东西折磨着我的精神。
那个厂里几乎所有的老职工都相互认识,谁家的什么情况彼此都了解和熟知,而人有时候并非是完全善良的,相反是爱嚼舌根甚至是恶毒的。我想用“恶毒”这个词来形容,我还想用“笑贫不笑娼”来描述。他们经常拿一把看不见的刀折磨一个千疮百孔的家庭,以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随意的践踏一个家庭的“尊严”。只因为那个家当时看起来很“弱”,有些“不光彩的事”,“贫穷”,“别扭”。他们总是用一种固有的眼光去看待那个家庭。我恨他们。我庆幸自己逃离了那里。
我离那里越来越远,偶尔回去那里,眼里看到的是斑驳。那里承接了我的童年,少年,但19岁之后我就离开了。再回去是23岁,再离开是27岁,如今的我37岁了,离那里越来越远了。那里的房子变得破旧,一些房子几经转手已不再是原来的主人,厂里的“原住民”越来越少,我从小到叫着“叔叔阿姨”的人们基本上都到了退休的年纪。
记忆中的厂房、办公楼、篮球场、车棚,花园、食堂、澡堂子……许多许多“企业办社会”的痕迹,一个厂可以承接工作、生活和学习,还可以承接一个人的成长。那里埋藏着许多童年的故事: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因为父亲打了她而逃到办公大楼里躲了一下午,等孩子的母亲回来,孩子的父亲笑着和母亲说,你看“我打她,她知道跑了”。还有许多许多的故事,越往前推,越是轻盈。那个花园里原来有座假山,假山的山口还有水往下流,一个几岁的孩子一点也不怕,非要爬到那个山口去洗手,被厂长爷爷看到了,还不敢大声喊她下来,怕孩子受了惊吓。那个花园里有两颗大的桂花树,一颗开黄色的桂花,一颗开金色的桂花,树的旁边有个小亭子,小孩子会踩着亭子下的石凳把手攀到亭子上的栏杆上荡秋千……
而现在故事里的小孩长成了大人,大人又有了小孩,时代在变化,物质变得极大丰富,那些记忆尤显得遥远而单纯。
*以上内容节选自作者的每日书写作
在每日书,记录你的生活和情绪
11月每日书报名中,期待你的秋日书写!
点击小程序报名
